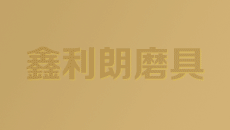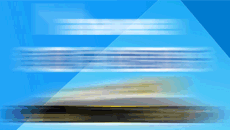那年那月,那坑口嘴那工村
□王景峰 图/文

1956年的运矿小火车头

仓库般的大平房。
历史回声
一个偶然场合,不经意间看到一本粤北英德地方文史资料———《三隅风情风貌》,我饶有兴味地浏览着书中这些熟悉的地名:仙桥、坑口嘴、横石塘、工村……忽然间,目光停留在五个黑体字上:英德硫铁矿。这可是当年载入中学课本、也是伴我度过少年时光的魂牵梦萦之地啊!当我读完矿山简介后,眼前不禁浮现横跨北江的架空索道,耳旁再度响起划破夜空载满矿石的小火车笛鸣声……
新世纪当我邂逅英德硫铁矿党委书记胡可听同志时,矿山已枯竭关闭;听他说起因时隔久远,矿山早期历史鲜为人知、这段饱浸前辈汗水的创业史几成空白时,不禁唤起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
1953年,一个新中国工业化建设高潮正在掀起,伴随着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一大批北京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响应号召,拖家带口告别京城,和从沈阳、抚顺、草河口抽调的职工一道,南下广东,支援矿山建设。
呼啸的南下列车满载着英姿勃发、即将成为新型矿山第一代职工的干部、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颠簸了五天五夜,于一个漆黑的子夜在一个孤寂冷僻的小站停了下来。几间平房,没有电灯,众人就着煤气灯一看站牌,上书“英德”两个大字。就这样,一行人踏上了这片尚待唤醒的南国山地。天蒙蒙亮众人来到江边,面对波涛,带队干部告诉大家,这就是珠江三大支流之一的北江。一行人挤坐矿山的“小火轮”溯江而上,几经辗转,抵达了一个被当地人称为“坑口嘴”的小码头。上了岸,在一座神似观音的岩石山脚下,带队干部手指两幢仓库般的大平房对众人说:“到家了”。
这是两幢砖泥合砌的大平房(图),每幢房里又分隔成十余间小房,约莫七、八个平方,小房之间的隔墙还没两米高,更没有天花板,南下的北京人每户挤住一间小房……你可别小瞧了这两幢大平房,它可是矿山第一代创业者南下的第一站,开拓者们就是以这为起点,坚实地迈出了建设矿山的第一步。自此,这个一没挂牌二没厂门、却是直属中央轻工业部的新型矿山宣告了自己的诞生,她的全称叫“国营英德硫铁矿”。
坑口嘴实际上只是矿山的转运站和家属生活区,真正的矿区还在北面四十里外的深山凹。每天早上天不亮,职工搭上卡车到矿区上班,下班坐在满载矿石的车斗上返回坑口嘴,回到时天已全黑,上下班成了名副其实的“两头摸黑”。英德北部背靠莽莽群山,地势突兀险峻,解放前兵匪肆行,即便到了1953年,山间仍有漏网土匪,有时睡到半夜,外面砰砰几声枪响,大人小孩缩在被窝抖作一团。而且,时不时还有“大虫”下山,一次夜间,运矿卡车就曾在路上遭遇老虎。考虑到安全,矿上为领导和部分中层干部配备了驳壳枪。
孩子们同样在经受各种考验,这儿解大便没有手纸,厕所门口摆着半筐竹签,是供解完大便刮屁股用的。孩子们哪能刮好?不时将屁股刮破。更有瘴气弥漫,胳膊、腿上起了好些水泡,一时无处医治,就从灌木丛中折下荆棘将水泡捅破,伤口和衣裤粘在一起,晚上一脱衣服,连皮撕下,血肉模糊……工作和生活异常艰苦,加上语言不通、水土不服,一些援粤人员撑不下去,不到一年就打退堂鼓了,举家老少返回京城……
可多数人还是坚持下来了。
村镇北面是所当地唯一的小学,矿山职工将子女送来这里就读。学校最高是三年级,一些已经在北京上了四年级的学生也只能“屈就”三年级。全校只有一位老师,三个年级每级一个班,全部课程由一个人教,经常是老师给一个年级上课时,另外两个年级就自习……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由于这些来自北京的矿山子弟就读,使得这个偏僻闭塞山村小学的普通话得已超前推广普及。
粤北依山傍塘的农舍飘出阵阵客家山歌———“吃的黄连吃的苦瓜,想吃那猪肉想脱(掉)了牙……”说来这山歌还是解放前的,新山歌尚未流传开,农民仍唱老的。在这片岭南贫困的地区,农家子弟好些都是十几岁才念上书,二十岁还戴着红领巾也见怪不怪。一坐落在贫瘠山凹的横石塘小学开学了,本该上六年级的小学生里一位叫“亚银”的女同学没来报到,大家一问才知道,她大喜了。
从1954年阳春三月起,坑口嘴的大平房里就相互传递着一个催人振奋的好消息:矿上要在横石塘北面不远的地方兴建“工人村”。没多久,“工人村”破土动工,往返于矿山的职工每天都向家属们传播着“工人村”的最新工程进度,更有那绘声绘色的描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要知道,这在当时可是人人向往的幸福生活呀!由于第一代南下职工许多来自东北重工业基地,当时普及于沈阳、抚顺等地的“工人村”发展模式顺理成章地被移植到了英德硫铁矿,这就是建于横石塘辖区内文峰附近、后来被称为“工村”的英德硫铁矿机关办公区和家属生活区。六十多年来,经人们代代相传,“工村”这一称呼一直沿用至今。
告别了坑口嘴,告别了两幢仓库般的大平房,全矿上下举家迁往工村,英德硫铁矿也从此步入正规化,向着新型的现代化矿山迈进。创业难,也正因其难才刻骨难忘;起步艰,也正因其艰才催人奋进。
1955年建成的工村,新房栋栋,清一色的砖瓦房———宏伟的大礼堂兼饭堂,乳黄色的二层办公楼,一排排的平房宿舍,职工医院在一片环境优美的小树林旁,不久又设立了粮店和消费合作社,马路旁建起了邮电所,幼儿园也成立了,“瞧!那是陈矿长家的小阳阳……”随后,灯光篮球场、游泳池、俱乐部、图书室相继建成,又开辟了一大块空地,兴建了体育场———四周是环形跑道,中央是足球场。
作为英德硫铁矿办公区和生活区基本构架的工村,她的建成为企业日后发展奠定了稳固的战略基础和切实的后勤保障。人心安定,职工没有了后顾之忧,推动了矿山生产的迅速增长,随着矿产量的不断提高,原先由樟坑至坑口嘴转北江装船的公路运输线已无法适应日益发展的运输需求,于是,一个铁路运输规划蓝图赫然而出……其实,规划蓝图从实施到建成也就一、两年时间。1956年,一条西起樟坑东至北江边的矿山小铁路运输线建成了,矿山从此告别了汽车公路运矿史,矿石沿小铁路运到北江边,经跨越北江的架空索道至冬瓜铺装车直上粤汉铁路……
即便是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当时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建成小铁路运输线,也堪称奇迹。小铁路几十里,穿村越庄,沿途征地一路绿灯,农民们积极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开山辟路中的许多重活累活都是当地农民干的,就连横石塘小学的学生们也在老师带领下参加筑路劳动,大家都以能为小铁路建设出一份力感到骄傲和光荣。当1956年小铁路通车时,连远在大深山里的瑶胞都扶老携幼前来一睹这“不吃草的铁牛”。崭新的小火车头上醒目地印着“波兰———1953”,毫无疑问这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最新型的机车了。当那来自东北、头戴“崇伦帽”的火车司机充满自豪地拉响了汽笛时,伴随着被大山反射回来的长长笛鸣,围观的人群爆发出阵阵欢呼,那欢乐气氛好似过年一般。
若干年后,这些当年曾参加劈山筑路的农民,这些曾为筑路出过一份力的红领巾们,许多人光荣地加入到英德硫铁矿工人阶级队伍。他们或下井,或驾驶小火车,或成长为工程技术人员甚至踏上了矿山领导岗位,当之无愧地成为矿山新一代的主力军。
生活安定平和,人心积极向上,带来的是矿山生产节节攀升,不但那些来自大都市的职工安心落户,甚至一些高素质人士、华侨乃至外籍人士也慕名而来———机关办公楼前,一位秀丽端庄的年轻姑娘迎面走近,胸前雪白的短衫上佩戴的校徽令人瞠目:“清华大学”。俱乐部的乒乓球室,经常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的归国华侨在打球,一看那海底捞月式动作,就会联想到姜永宁和匈牙利名将高基安。干部宿舍南排,住着日本工程师酒井喜作和他的家人,关于这位日本工程师,矿上流行许多有关他的故事,最神奇的版本是:只要他用手中的拐杖往地上敲几下,便知下面有矿没矿。
矿上人才济济,男篮多次代表工业系统远征,球衣醒目地印着五个大字:“广东重工业”。一位来自广州的职工竟能跳出两腿笔直、双手碰脚尖的高难度跳水专业动作“101B”。最难得的是足球,这儿可能是全英德开展足球运动最早的地方了,难怪多年后工村能走出一位先在国家女足、后在美国费城冲锋队踢球的大名鼎鼎的“阿猫”赵利红。
从工村的广播能听到那个时代最为流行的歌曲《半个月亮爬上来》《在那遥远的地方》,球场的露天银幕能看到最新影片《翠岗红旗》《神秘的旅伴》,大礼堂前的阅报栏上,能读到最新一期的《体育报》。人们对打破世界纪录的陈镜开、戚烈云耳熟能详,对蓝亚兰的自由体操和杨伯镛的飞身上篮津津乐道……
经过四年的拼搏,英德硫铁矿已经今非昔比、名声在外,甚至上了当时的中学地理课本,就连誉满岭南的华南歌舞团也不辞辛苦地翻山越岭来到工村慰问演出。北京话、广州话、东北话、湖南话、客家话兼容并蓄,京剧、粤剧、二人转、客家山歌、西洋女高音宛转悠扬———幕天席地的工村,有着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多么令人神往的图画,多么催人陶醉的音符,那一幕幕、一瞥瞥,犹如广东民乐《彩云追月》一般勾魂摄魄永不散去。
经过四年的磨砺,这些来自北京的矿山子弟,铿铿嘎嘎都能说客家话了,也学会打赤脚了,一扫当初的细皮嫩肉,光脚能在荆棘丛生的荒野中奔跑了。就连下乡支农解大便没有手纸时,用竹签刮屁股居然也刮得很溜了……四年的交融,南下子弟和当地小朋友们结下了深厚友谊,和教授过自己的山区老师结下了割不断的师生情,这种情谊在日后的生命长河中珍存了数十年,甚至维系一生。
六十六年过去了,如今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雨的坑口嘴两幢仓库般的大平房已经拆除,昔日的工村也变了模样。但巍峨的观音岩和五郎嶂依然屹立,它见证了英德硫铁矿创业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向世人诉说着第一代南下创业者的奋斗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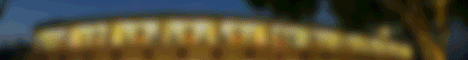
 新闻聚焦
新闻聚焦